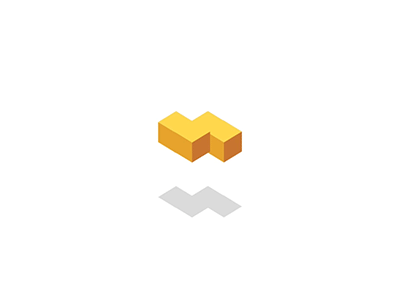一、文本解读的争议与辨析
亲亲相隐思想见于《论语》子路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孔子与叶公的这段对话中有三个关键字攘、直、隐。学者们对亲亲相隐思想的讨论也多是围绕这三个关键字的理解展开,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三个关键字的含义分别进行讨论:
(一)攘:对行为目的的理解
从攘这一行为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行为者的动机。郑玄认为,直躬者之父攘羊之攘是盗窃之义,亦即此举乃有意为之,皇侃亦作此解。另一种解释则减弱了行为目的的恶意性,将攘理解为顺手牵羊、路边拾遗。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用《淮南注》对攘的解释即是如此,朱熹亦持此解。作为当代学者中维护亲亲相隐正当性的代表,郭齐勇也支持顺手牵羊的解释。或许在学者们看来,对于行为目的的恶意与否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对亲亲相隐思想的最终评价。
(二)直:关于行为者依据的三种理解
在《论语》孔子与叶公的对话中,涉及两种直,前一种是为叶公夸赞的,检举父亲的那个直躬者之直。后一种则是孔子心目中与之相异的直者之直。前一种直的理解相对简单,其含义基本上是对行为事实的描述,权且将之当做一个人名代号或称其为直率之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后一种直的理解,即孔子心目中真正的直者的含义。总结古今学者们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解释:
1.情感论。在古代,这种解释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依循其理学思路,他将父子之情与天理相联系,认为只要是出自对于父亲的真实情感,子女的行为就不会不合天理,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现当代学者中,情感论亦不乏支持者,代表人物是冯友兰和李泽厚。冯友兰将直理解为人的真实情感(内)与外在行为(外)的内外统一性、一贯性。在其父攘羊事件中,儿子不愿意父亲因攘羊之事暴露而受辱,这是出自人的真实情感,所谓直者由中之谓,称心之谓。李泽厚则对直义之古今理解作了区分。他强调孔子心目中的直,并非我们今人所理解的社会正义、法律公平,而是指情感上的单纯性、真实性。我们可以承认情感论的合理性,但亦不可否认其缺陷:行为者真实的情感,作为其行为动机,并不必然导致好的结果,这一点想必毋庸赘言。要想将其父攘羊这一事件妥善、完满解决,单凭情感的真实性远远不够。
2.理-分论。这种解释最早或可见于东晋学者范宁的言论: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谓直也。而将之作为一个理论解释提出的则是劳思光,他认为,理-分论将每个人的行为准则的根据归之于其所处的身份与位置。判断一个人是否直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是在履行分内之事,就作为儿子而言,对待父亲不能像对待路人一样,对于路人而言,举报一个攘羊之人似无可指责,但作为儿子来说,举报自己的父亲则不合其理-分。 理-分论亦有其可取之处,但与情感论一样仍然没有给出一个能够实现好结果的具体方法。而且,过于为人的行为划定理-分的界限,理-分论便也会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是单一的,我们作为子女固然有子女之理-分,但是同时又作为社会公民,也有须履行之理-分。如何处理不同理-分之间的冲突,似又须援引新的根据。
3.情-理融贯论。这种解释以郭齐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主张。这种解释可谓对情感论的完善:一方面,与情感论一样,情-理融贯论的支持者们坚持人们的行为应当依循内心的真实情感;瑏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里的直,不是单纯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寓情于理之直,是在具体情境之中区分情感和理性,妥善处理公私关系的智慧。这种解释似乎是最为妥帖的一种解释,但仍有可商榷之处。在其父攘羊事件中的情与理的融贯,他们的解释是通过对情境的具体限定实现的,即一方面通过主张攘是顺手牵羊之意来减弱行为的恶意性,一方面又通过主张隐意味着不作为而非隐瞒、包庇,来缓和情与理之间的张力。这样的限定就必然影响到了情-理融贯论的普遍适用性。孔子心目中真正的直,除了情与理的融贯之外,还应该加上事这一层面,亦即情-理-事三者的统一。而事则是指具体的行为方式。从以上三种解释中我们似乎只能看到子女的消极不作为,关于子女应该从积极的方面采取何种作为的问题,我们只能从隐的理解中去寻找答案。
(三)隐:行为的方式与准则
对隐的理解,结合古今学者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观点:首先是缄口论,郑玄对隐的理解就是不称扬父母的过失,这是缄口论中的消极不作为一面。就其积极作为一面而言,当代有学者主张将几谏纳入缄口论的主张中,作为一种劝谏父母改错的行为方式。同时,几谏还是一种有效的行为预防方式,几谏除了有委婉劝谏的意思之外,王夫之还将之扩展为见微而谏、防微杜渐的含义。从理论上说,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在源头上消弭情与理的紧张关系,避免了真正酿成大错而不得不面临艰难抉择的伦理窘境。其次是檃栝论,这种说法是近年来学者提出的一种新论。该观点将隐理解为檃栝,原义是矫正木材弯曲的器具,引申为对人的行为的矫正。另有学者提出与之类似的伏灭论。这两种解释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虽然就字义的解释而言,这两种解释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但是就理论本身而言,它们强调的具体行为方法上实质上与几谏无异。故而檃栝论与缄口论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只是彼此的侧重有所区别。
此外,隐匿论在古代亦是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说法,朱熹便持此观点,并以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的例子为之佐证。 这种说法最早可见于《盐铁论》。 但是隐匿论在当今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古代,或许是因为在当代人看来,隐匿论的主张明显与社会公义相悖。而且从维护亲亲相隐思想正当性的角度来说,采取隐匿论的观点,会大大加重我们的论证难度。
(四)以上诸论的总结
就隐的理解的三种观点来看,除了隐匿论之外的另外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几谏的不同说法。不论是事前的防微杜渐,还是事后的委婉劝谏,都难以提供社会公义与父子亲情的现实张力的切实的解决方法。
之所以说这两种观点拿不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是因为缄口论主张不称扬父母的过失,这固然也是一种解决办法。但这种办法究其实质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在现实的具体情境中难以实现其保护父母不受伤害的初衷:我们可以想象,一方面,如果当失主向攘羊之人的子女来询问羊的去向,子女很难闭口不言,如果子女向其隐瞒了自己父亲的行为,这样的做法本身就不再是缄口论的主张而滑向了隐匿说;另一方面,如果父亲攘羊的证据已经被官府所掌握,那么子女这时候的不作为也就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不论是缄口论还是檃栝论,对于这样的情况都难以给我们提供合适的行为选择。在上述众多观点中,针对其父攘羊的具体情境能够向子女提供积极行为措施的观点只剩下了隐匿论。但是当代大多数学者之所以不采用隐匿论,理由上文已经提及。不过在看笔者看来,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隐匿论的主张与社会公义完全相悖,而应该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对两者的关系加以审视。
二、隐匿说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合理性
(一)攘羊的量刑标准的考证
关于攘羊的问题,古今学者往往只讨论攘羊之攘的字义辨析,纠结于攘羊究竟是顺手牵羊还是恶意窃羊,而很少关注攘羊这一行为在当时作为一种犯罪行为的量刑问题。但事实上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隐匿说的合理性的判定。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攘羊作为一种犯罪行为的量刑标准在当时是极为严苛的,以《吕氏春秋当务》对其父攘羊事件的记述为例: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直躬者请代。将诛,告吏曰:夫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诛。孔子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无信。
《吕氏春秋当务》中记载直躬者的父亲的罪行是窃羊。从文中可知,这种行为在当时的刑制下,会被处以死刑(诛)。作为佐证,董说在《七国考》中,引用了刘向的《孟子注》,对于当时楚国的刑罚进行了描述:楚文王墨小盗而国不拾遗,不宵行。至于说为什么楚文王对小盗的行为施以墨刑而国人便不敢拾遗,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拾遗与小盗的量刑标准是一致的。第二种解释是拾遗与小盗难以区分。就像在其父攘羊事件中,直躬者的父亲到底是恶意窃羊还是顺手牵羊,恐怕不但我们当代人不清楚,当时的人同样难以调查清楚,所以官府采取疑罪从严的标准,故而国不拾遗,不宵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纠结于攘羊的真实含义便失去了讨论的价值。除了这个例子之外,我们还可以再举战国法家李悝在《法经》中的论述: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李悝生活于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相去不远的战国早期,他的言论也代表了当时重刑罚的普遍观点。其中提及的刖刑不仅仅是魏国的专利,在楚国也有被使用的记录,最为著名的例子便是昔卞和三献和氏璧的故事中,卞和两度遭到了刖刑。由这些例证可以看出,是否解开了直躬者之父攘羊的谜团,并不影响我们做出他极有可能会被施以肉刑的判定。就攘羊行为会受到的具体刑罚而言,总计上述三处例证中的刑罚,最重的刑罚是死刑,其次是刖刑,再次是墨刑。另外,《韩非子》对于其父攘羊也有一番记载:楚之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屈于父,执而罪之。在这里,直躬者的结局虽然与《吕氏春秋》中的结局迥异,但是也透露出了相似的信息,即直躬者被杀的原因既然是直于君而屈于父,对于他陷父亲于险境的处罚死刑,父亲原本应该遭受的刑罚应该与之相近。故而直躬者之父原本应该遭受的刑罚与死刑应该相差并不悬殊。总结来看,直躬者之父所遭受的刑罚极有可能大于等于刖刑,小于等于死刑。
(二)社会公义与孝子之责
在当代法治社会中,法律显然不可能规定对攘羊行为处以死刑或肉刑,对攘羊行为处以类似刖刑、墨刑等残酷肉刑,这样的刑罚毫无疑问在当今社会超出了维护社会公义应有的限度。当然,要证明隐匿说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合理性,除了证明刑罚的残酷性之外,还必须阐明这种残酷的刑罚在当时是否符合社会公义,而不能完全以当代人的视角对其加以简单判定。
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楚才晋用的典故为例。声子作为出使楚国的蔡国使节,与当时楚国令尹讨论楚国与当时另一春秋强国晋国的人才问题时,声子认为,从理论上看,不论是人才的数量还是质量,晋国都难以与楚国相较。但就事实而言,楚国的大量优秀人才正源源不断地为晋国所引进。对于这一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人才流失问题,声子敏锐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楚国的人才流失之所以如此严重,在于楚国淫刑太多,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淫刑就是包括许多肉性在内的酷刑。士大夫尚且不能忍受残酷的刑罚,庶民对其认可程度也就可想而知。由此不难想见,如此残酷的刑罚,不仅不为当代人所认可,即便是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对之难以苟同,所以对于隐匿说的主张与社会公义完全相悖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使父母免于酷刑之辱,是为人子女的责任。正所谓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史记》中缇萦救父的典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缇萦为了营救被陷害下狱,即将被处以刖刑的父亲,上书给当时在位的汉文帝请求免去父亲的肉刑,文帝为缇萦的孝心所感动,不但赦免了缇萦的父亲还一并废除了肉刑。
通过上述对直躬者之父可能遭受的酷刑的讨论可以发现,我们决不能不顾古今刑罚存在的巨大差异,完全以今人的视角去批评隐匿说,甚至对亲亲相隐思想加以完全否定。当然,酷刑毕竟只是作为一个外在的特定条件,并不足以作为支撑隐匿说甚至亲亲相隐思想合理性的必要条件与根本依据。否则的话,一旦抽离了这个特定条件,亦即在法治日益完善健全的当今社会,子女是否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举证父亲的罪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回到其父攘羊的事件中,孔子之所以不认同直躬者的做法,并不完全在于他的父亲最后是否得到赦免,免于酷刑,而更是在于直躬者证父的动机为取直名。正所谓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这里的直名之直,也就是叶公所夸赞的直率的行为,而不是孔子心目中的直,即情-理-事的统一。这也就要求子女的行为不但出自真实的内心情感,履行子女的指责,兼顾社会的公义,最后还要取得满意的行为结果。为了说明实现这样的统一,尤其是取得满意的行为结果,我们就要对亲亲相隐之隐做出具体的方法论区分和要求。
三、隐的三个层次
(一)隐与几谏
在关于隐的几种解释中,不论是传统主张的缄口说还是近年来学者提出的檃栝说与伏灭说,都可以从《论语》中的几谏找到其思想源头: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对于几谏的理解,传统的解释指的是委婉劝谏,王夫之将之引申为见微而谏。虽然钱穆认为王夫之的理解从语法的角度上还值得商榷,但是从文义上而言,王夫之的理解不啻是对几谏内涵的一种扩展。从方法论层面上说,委婉劝谏侧重的是父母在已经犯错之后的改错的方面,而见微而谏侧重的是平时的预防工作。在这里,几谏之几是隐的具体方法论要求。既然几谏的内容是见微而谏与委婉劝谏。所以在具体的行为方法上也就要求子女不论是在平时对待父母还是向父母几谏时,都要要做到色难: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这里的色,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指父母之色,即指子女在与父母相处时,能时时关注父母的颜色,由此体会父母的心意;另一种解释认为,色是指子女对待父母时和颜悦色。而关于色难中难的含义,朱熹采纳《礼记》中祭义篇的解释:盖孝子之有深爱,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所以他认为,在与父母相处,侍奉父母的时候,最难的是能够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不过倘若将子女对父母的深爱作为克服色难的充要条件,那么这里所谓的难也便如为长者折枝一般,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但是在其父攘羊事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出这里的难处,即如何在不伤及父亲感情的基础上帮助父亲改正过错。
其中,对待父母时和颜悦色显然与几谏之几相关,不论是见微而谏还是委婉劝谏,都必须要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一方面要避免或弥补过错,一方面也不能因此而使父母恼怒伤心。所以,在其父攘羊事件中,隐的对象不仅仅包括丢羊的失主与司法机关,还应该包括直躬者的父母。
(二)敬与为父而隐
之所以在劝谏父母之时要和颜悦色,不能伤及父子感情,其根据在于敬: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孝与不孝的根本区别在于敬。《盐铁论孝养》云:孔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不敬,何以别乎?故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所谓养色,即色难之色,既可以是父母的颜色、心意,也可以是子女侍奉父母时表现出的和颜悦色。这里提到的孝的最高层次的养志,最早出自曾参侍奉父亲的故事: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馀,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可也。《孟子离娄上》曾元在侍奉父亲时,只是以自己的想法做事而没有顾及到父亲的意愿,即便父亲表面上没有表示,想必心中已有郁结,从方法上说,曾元没有做到养色,而其根源在于不顾父亲的意愿,所以孟子认为他没有做到养志。我们可以将养志看作是子女在处理父子关系中对父母的敬的实践表现。就养志与养色的关系而言,养色是养志的方法要求,而养志则是养色的行为动力与目的。
对父母之敬应该体现在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所有情境之中,不论父母处于何种境地,子女都应该对父母持敬,也就是父子一体,荣辱相及。子女从小受父母养育教导之恩,对父母心存敬意似乎不难。但是当父母犯错,处于道德与人身双重困境之时,仍能对父母持敬,这种一以贯之的敬才是子女对父母真正的敬。因为这意味着子女始终会在与父母的互动关系中考虑自己的行为,并将父母的荣辱功过纳入到对自身的行为评价之中。在其父攘羊事件中,出于对父亲的敬意,一方面子女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为父亲改错,弥补父亲的过错;一方面子女在劝谏父亲之时也应该注意合适的方式,不能不顾父亲的意愿,伤及父子之情,更不能够像直躬者一样,通过检举父亲的方式,陷父亲于困境并获得直名。
(三)隐的三种层次
结合上文对残酷刑罚与社会公义关系的讨论以及对《论语》中相关思想的分析,再加上古今学者的讨论成果,从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双方面结合考虑,我们可以将隐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其萌芽处隐,即预防措施。子女在平时应该注意观察,对于父母平时一旦有犯错的苗头,子女要及时发现并及时劝谏。防微杜渐,将犯错的苗头消弭在萌芽之中。但是在劝谏时,应该采用委婉和善的方式,要顾及到父母的感受。而且在劝谏之时,子女要认识到父母的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不能将自己视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父母进行道德评判的旁观者。第二个层次是在其犯错时隐,即弥补措施。倘若父母已经犯错,并且造成了他人的损失,一方面,子女应该代替父母,尽量补偿对方的损失并争取获得其谅解;一方面,子女还要委婉地劝谏父母,在这一过程中要与父母积极沟通,尊重父母的意愿,既不能够直陈父母的过失、无视父母的感受而使父母恼怒,也不能够让父母伤心愧疚,认为自己拖累了子女。
第三个层次是使父母免于不合理、过度的刑罚。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不仅是对受害人,同时对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也会加以保护,这一点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代人的基本常识。在当代社会,如果父母不幸入狱,我们可以通过为父母聘请律师、及时弥补受害人损失等手段,为父母争取减刑。而在春秋时期,法律缺少对人们正当权利的保护,为了规避残酷的肉刑,子女采取隐匿的措施对父母的人身安全加以保护,根据上文的论证,并不与社会公义相悖。
最后,在笔者看来,隐的意义不应该仅仅只是停留在对于父母犯错时,作为危机处理的一种措施,同时还应该作为父母与子女日常相处时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隐不同于源自西方的所谓隐私权,后者先是将父母与子女的生活领域现成化,然后在这之上划定界限,活生生割裂出一个父母不可涉足的子女的私人领地。与孔子的隐的意义相比,似其形而未达其意。父母与子女的生活情境并不是像签订合同一样,规定双方的行为规范和界限。如果说这个情境有彼此的界限的话,那这个界限一定是模糊的,同时在整个情境当中也充满了许多不清晰、模糊的区域。子女不应该急于将这些区域变得清晰化、现成化,而应该将之作为酝酿出无限生活可能性的源泉,隐而未发,伺机而动,这也就是养色与养志的要求。